配资在线配资炒股 成都银行,警示函背后的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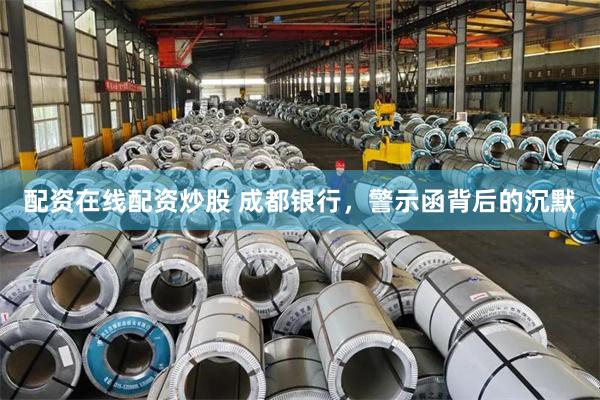
导读:成都银行能否在风雨飘摇中稳住船舵配资在线配资炒股,重回增速巅峰。
成都银行,作为区域金融领域的佼佼者,近期却风波不断,暗礁潜藏。从信披违规的疑云,到业绩增速的下滑,再到过高的拨备覆盖率和居高不下的贷款集中度,一系列问题如同警钟长鸣,提醒着人们其正面临严峻挑战。
2025年初,一封来自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的警示函,更是将成都银行在基金销售业务方面的违规问题暴露无遗。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这则警示函并未在成都银行的公告中现身,其对信披规则的轻视态度引发广泛质疑。与此同时,成都银行的业务层面也隐忧重重,加之董监高人事变动频繁,新业务掌舵人能否扛起重任呢?
警示函未公告,信披规则何以被轻视?
2025年1月6日,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的官网上,一则针对成都银行的警示函悄然浮现。警示函中,明确而严肃地指出了成都银行在基金销售业务方面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内部控制制度的不健全、部分基金销售人员未取得应有的基金从业资格、内部考核机制的不完善……这些行为,无一不严重违反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图片
按照常规的监管流程,当一家上市公司收到此类警示函,并被要求在30日内书面向监管部门报告整改情况时,它理应及时、主动地将这一重要信息向广大投资者进行公告。这不仅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明确要求,更是对投资者知情权的尊重与切实保障。
然而,当我们仔细翻阅交易所的公告系统,查阅成都银行自2024年12月至今的所有公告时,却惊讶地发现,关于这则警示函的公告竟然无影无踪。
这种对监管措施的沉默态度,无疑是对信息披露规则权威性的公然挑战。成都银行的这种行为,让人不禁质疑其对信披规则的重视程度究竟几何。
信息披露规则,作为资本市场的基石之一,其存在的意义在于确保信息的透明与公正,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面对监管部门要求提交书面整改报告的严肃要求,成都银行是否会认真对待并切实落实?从其未及时公告警示函的行为来看,答案显然并不乐观。
成都银行已经违反了上市公司的信披要求,而这一违规行为背后所折射出的公司治理问题,更是值得我们深入剖析和探究。
业绩增速放缓,繁华背后的隐忧
当我们将视线从信披问题转向成都银行的业务层面,会发现其繁华表象之下,实则暗流涌动,隐藏着不少隐忧。
图片
根据成都银行2024年的业绩快报,该行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29.77亿元,同比增长5.88%,归母净利润更是达到了128.63亿元,同比增长10.21%。同时,不良贷款率同比下滑0.02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依然维持在479.28%的行业高位。初看之下,这些数据似乎勾勒出一幅业绩稳健、前景向好的画卷。
然而,当我们拉长时间轴,深入剖析成都银行过往的业绩数据时,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逐渐浮现。在营收增速方面,从2021年的22.54%一路下滑至2024年的5.88%;归母净利润增速也同样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从2021年的29.98%跌落至2024年的10.21%。这种业绩增幅的显著下滑,无疑为成都银行的未来发展投下了一层阴霾。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不良贷款率看似下降的背后,重组贷款和逾期贷款的快速增长却如暗流般涌动。以2024年半年报数据为例,截至6月底,成都银行的重组贷款较年初增加了2.2亿元,总额达到18.54亿元,其中不良贷款占比高达12.44亿元。
而逾期贷款方面,更是从2024年年初的49.88亿元激增至63.5亿元,短短半年时间,增长幅度接近30%。这种重组贷款和逾期贷款的迅猛增长,无疑给成都银行的资产质量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让人不禁期待2024年全年的数据能够揭示更多的真相。
此外,成都银行的高盈利背后,是高分红和高拨备的双重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其利润空间。同时,该行的资本充足性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且呈现出连年下滑的趋势。尽管该行已积极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和金融债来补充资本,但其资本充足水平仍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这无疑为其未来的稳健发展埋下了隐患。
风险管理能力受挑战
在成都银行的发展历程中,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信披违规引发的信任危机、业绩增速下滑、高拨备覆盖率以及贷款集中度高等业务层面的问题,却如同警钟长鸣,时刻提醒着人们其正面临的严峻挑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成都银行自身的生死存亡,更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图片
除了高拨备覆盖率之外,成都银行的贷款集中度问题同样值得高度关注。截至2024年6月底,其前十大客户贷款总额已高达456.15亿元,占同期资本净额的41.35%,在17家A股城商行中,仅次于西安银行和兰州银行,逼近监管部门设定的50%上限。
回顾近几年,成都银行的贷款集中度呈现出快速攀升的态势。2021年至2023年,该行前十客户贷款比例分别为34.37%、38.35%、37.5%,而到了2024年,这一增长趋势愈发显著。尤其是单一最大客户的贷款比例,从2021年的4.72%逐年上升至2023年的4.81%,至2024年6月底更是陡然飙升至5.48%。
过高的贷款集中度,对成都银行而言,犹如一把高悬头顶、摇摇欲坠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旦这些大客户出现经营困难或信用危机,将如多米诺骨牌效应般,对成都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经营业绩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这种高度集中的贷款结构,不仅极大地增加了银行的经营风险,更对其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中,成都银行能否妥善应对这一挑战,有效化解贷款集中度过高带来的潜在风险,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2024年12月,成都银行宣布因股价触发赎回条款,将提前赎回“成银转债”。这一决定令人颇感费解,因为可转债是银行补充一级资本、降低融资成本的重要途径。此次赎回导致第二大股东丰隆银行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无疑给成都银行的股权结构带来了一定的变化。
在成都银行业务转型的关键时期,该行董监高也频繁出现人事变动。2024年人事变动次数更是增至18次,其中包括行长的换任。新行长徐登义于2025年5月就职,面临着与原领导班底的磨合问题。
同时,董事长王晖的7年轮岗期限届满,或将迎来换任。此外,部分副董事长、副行长等高层管理人员也已任职多年,面临着新老交替的局面。
新行长徐登义作为空降人员,不仅需要与原领导班底进行磨合配资在线配资炒股,还要应对即将到来的董事长换届。新的掌舵人能否带领成都银行重回增速巅峰,还需时间的检验。
